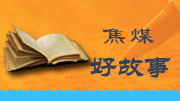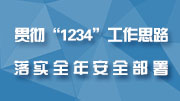那是一个夏天。爬满树梢的叶子绿得直逼人的眼,埋伏在枝头的知了扯着嗓子拼命喊,街头四下流窜的车流人河灼烫每个人的脸。就在这样一个骄阳当头的午后,我和几位亲戚挤在一辆出租车里去筹备另外一个亲戚家的婚礼。
车子行驶的街区,是这座城市里我不熟悉的一部分,虽然说不上“最”。汽车音响压低嗓音放着一首欢快的歌,大家有一搭没一搭地谈着将要去的亲戚家的陈年往事。忽然,窗外飘过一个大大的招牌,“正版图书特价处理”,托着一个不大醒目的匾额。赶紧问一位经常在附近出没的亲戚这是什么地方,得到的回答是“××路”,心里便默默记住。
当晚,从亲戚家回来,趁着还有印象,赶紧问了度娘。先查询书店的名字,度娘像我一样茫然无知。再查“××路”,惊人的是,在那片区域里,竟然有着三条“××路”,只不过每一条路前头再戴上一个表示方向的帽子。幸好,那个地方的方向,我还辨得明白。在那个方向上,仍然有两条“××路”一前一后首尾相顾地趴在百度地图上。看看比例尺,算算实际距离,心里有了谱:从第一条路的起点到第二条路的终点,也不太远;书店在右手,找到书店就余下的路不用再走了!
次日正好是周日,出席过亲戚的婚礼,送外地的亲戚上了高铁,思谋着上了一趟开往那爿街区的公交车。果然,不太费劲就找到了那家书店。门脸不大,里边的进深却不算小,急就简陋到只有书和书架。沿着两边的墙和店的正中,摆着四排书架,或密或疏陈列着不少书籍。凭着直觉,我知道,“正版”不是妄言,再问价钱,都是五折的,心里便浸出丝丝凉意,额头的汗珠也渐渐消去了。
这里的书除了儿童读物,以文学居多。文学中诗词、散文类的不少,小说也间或穿插其中。出版单位以国内三家知名的出版社为主,丛书多,都分开销售。从出版日期上来看,大约是早先出版销售不畅以致积存的结果——跟今日的平常价格相比,还是合账的,况且又打了五折!
逡巡一周,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一个书架一个书架地过。边过边搜索,一本一本,挑到手里。回到起点,变成了一摞。站立柜旁,一本一本,略加翻阅,再做选择。原先端在手里的书摞分成了大小不一的两摞,一摞义无反顾欲购买,一摞犹豫踌躇待思量。再从后一摞中挑出几本,放进前一摞中。拿起剩余的几本,斟酌再三,恋恋不舍,放回原来取走的书架上。最后挑了张岱、侯方域、戴名世、方苞和袁枚几人的散文选集,另外还有李清照、姜夔的词,还有根据分类编选出的豪放词和婉约词选本以及从《花间词》中选出的选本。词的原文都未必陌生,只是研究者多起来,编出来的选本也多起来,比照着读也是一种乐趣。
书店由宽变窄的地方,快要接近门厅了,坐着主人,一位三十上下的少妇。短发,脸上很白,细看却是敷了很多粉,让人想起三国曹魏的何晏来,当然,性别不一样,可我还是想起了何晏。结账时却比我的粗估多出六块钱,于是重新算过,付了钱。捎带谈论几句书店经营方面的事情,说是原先在北京也做书店生意,想来此地开拓,发现读书的人远没有北京多,很有几分气馁。此处也做不了几天,因为附近有危房,因为要拆迁,更因为效益不好,打算往另外一条我比较熟悉的街道边搬家,“找一处闹中取静的地方”。
书店自然要找闹中取静的地方,这倒是符合经营之道的。热闹的地方,客流量大,喜欢书、喜欢读书的人多,销量才可能大,书店才得以生存;周边环境尤其是左邻右舍不能太过于噪杂,人声鼎沸更是要避之不及,读者才会安下心来翻几页书。得知我是穿过半座城专门过来看看书店的,少妇很惊奇。为了以后能够找到这家书店,我专门打开流量,扫了对方的二维码,互加了微信。
两个月的日子里我还去过那家书店好几次。有时候挑一些自己心仪的书籍带走,没有格外的兴奋;有时候空着手离开,也不会抱憾。购书,尤其是在这样的特价书店里,有无收获全部寄托给缘分,是最明智的选择。
平常见到的都是少妇,带着一个两三岁的男孩——第一次去时,男孩在不在,我是没有什么印象的。少妇不翻书,男孩也不翻书,有时候俩人挤在一处追剧或者跟一个似乎家居的男人聊天,有时候少妇一人追剧或者跟那个男人聊天,孩子就在一边的地板上玩耍。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个少女看店,偏偏我还选了几本书。少女很快就算好了价款。原来她是两本书一起算,比如,一本十八元的,一本二十二元的,记做二十元,放在一处。其他的再两两相碰,很快计算出来了。
无论是谁守店,上午开门都很迟,总要在九点半之后。有两次,我因大清早去了周末才有开张的旧书市场,再折道去了那家书店,门口都摆着满满一碗闭门羹,几乎等到耐心全部消磨殆尽的时候,才看见店主姗姗而来,一次是少妇,一次是少女。
再后来,那家书店就关张了,房门上张贴了招租电话,也不见有什么“本店迁至……”的字样或者电话。关张是这个时代书店的常态。我呆在那家书店的那些时辰里,遇到其他顾客倒是一件罕事——似乎只有一个半人进来,因为其中一个在门口问了一句“有没有孩子需要的××书?”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就抽回跨进来的一只脚离开了。
我想过到少妇说的那条街上去找可能搬迁到那里的书店,又摇了摇头。少去一次书店,少买几本书,日子还是一样过。终于有一天,我忽然想起曾经留过店主的微信,一阵搜索后才找出来,发了一句:“贵店搬迁到哪里去了?”几天以后,我在微信上得到了对方的留言。原来,那家书店搬到了百十里外的一个县城里。“太远啦!”我又留言。“过段时间说不定还回来,到时候发朋友圈告你吧。”这一次回复,不过间隔了两个多小时。
那家书店就这样暂时消失在我的生活中了。看了店主的回复,我很为她的自信或者念想担忧,因为这些年来,这类书店的消失我已经见怪不怪了,新开张的却凤毛麟角得很。
但愿在那个县城里,有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容下那家书店,有许多爱书的人养活了那家书店,直到永远。
(作者单位:集团公司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
- 上一篇:
-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