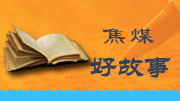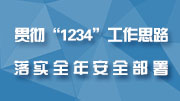我以为夏天还要再回来眷顾一番红尘俗世的,看那时他的热火劲,通宵达旦、鞍前马后地围着人转,全不顾人的眉眼脸色,只是喋喋不休地惹人烦,浑似一个多情郎。却不想,自处暑以来的两场雨后,他竟自若而去,一去不返,真像是一个负心人。如今,早晚秋凉如水,虫声细碎,想想那时的热烈,唯觉一片清寂。
看这本书也是夏天时的事,一本《前后汉故事新编》,仅是下册,里面许多人物,诸多传奇,读来很是过瘾。从“飞将军”李广、“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霍去病、牧羊的苏武、画眉的张敞到富春江上钓鱼的严子陵、“马革裹尸”的马援、“投笔从戎”的班超和“天知地知”的杨震,“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但有趣的要数几个东汉时的名士。
那些名士,按现在的道理说起来,各个都属异类。
生死朋友
山阳人范式与汝南人张劭都是太学生,两人交好,他们半途离开太学分别时,张劭请范式到他家做客。范式心里一合计,道:“而今事多,后年此日,定然前去拜访伯母。”
两年一晃而过,这一天,张劭在家请老母细备好酒好菜以待范式。他母亲责怪他说:“山阳到汝南(山东到河南的样子)山长水远,人家只是随口一句客气话,哪里就会来呢?即便要来,也不一定非是今天啊。”
张劭深信不疑地说:“范式最讲信用,他说今日来就一定是今日。”他母亲无奈,便杀了一只鸡。没想到鸡还没炖烂,有客登门,张眼一瞧,竟是范式。两人握手言欢,畅饮一番。范式坦言:“现今公务繁忙,今日特来赴约,明日便回。”第二天便真的回去了。
后来张劭害病,他的两个朋友每日去看,照顾甚周,但张劭仍念念不忘范式。两友很是生气:“我们尽心竭力地照顾你,你却心心念念只说旁人好呢?”张劭说:“你们的好我何尝不知,只不过,你们与我仅算是生前的朋友,范式还是我死后的朋友啊。”二人不解。
几日后,张劭没有好过来,不治身亡,待要下葬时,灵柩竟如有千斤之重,无法抬起。后有人从汝南到山阳,告知范式说张劭已亡。范式不信,晚上做一梦,梦里张劭说:“你若记得咱们的情义,能否替我安葬?”范式听罢,未及作答已涕泪横流于梦中醒来。翌日便向太守请假前往汝南。
范式的车马快到坟地,张母远远看到,拍着张的灵柩说:“你的生死朋友来了!”别人不信,待车至眼前,果然是范式,范式手扶灵柩,痛哭曰:“你我朋友一场,而今阴阳两隔,从此永别了!”众人闻言,皆纵声痛哭。如此,张劭方得安葬。
宁隐不仕
梁鸿与孟光举案齐眉的故事,知道的人很多。
梁鸿上学时,因为穷,为了生活,给人看过猪,替人打过工。学成归来后,完全没架子,下地种田,庄稼活没有不会的。大伙想着这么一位三好学生四有新人大好青年不做官又没娶上媳妇多可惜啊,给不了官,只好抢着要把自家的闺女给他当媳妇,但梁鸿一概拒绝了。
这个时候有个姓孟的大款,日子过得滋润,就是他家姑娘,名叫孟光,不肯出嫁。说媒的都踩破门槛了,她都不答应。老孟很恼火,说:“都要三十的人了,高不成低不就的,你要什么样的我都找得来,你倒说说啊?”孟光小姐说:“要我嫁,除非找个像梁鸿一样的才有得商量。”
老孟赶快托人找梁鸿。梁鸿想,既然人家铁了心思看上咱,也算是咱的造化,不能再摆谱了,于是同意。
孟光一听心花怒放,但爹娘给的嫁妆一概不要,只带了几身粗布衣服和一些女工。不想过了门,足足有七天,梁鸿都不理孟光。孟光左思右想,不解其意,有一天实在忍不住便上前问:“相公是有学问的人,择妻定然也是慎重的,我虽然相貌丑陋,但也不是谁都肯嫁的,我们既然做了夫妻,就该好好过日子,但您的不高兴所为何来?”
梁鸿叹气道:“我原想着你是个勤俭又朴素的人,谁想你穿金戴银,绫罗绸缎,我哪里配得上又哪里敢亲近啊!”孟光听罢,说:“原来如此。”立时退回屋内,除去首饰,换上一身粗布衣服出来。两人从此过上了幸福恩爱的小生活。
但有一天,孟光忽对梁鸿说:“我知道你不想做官,可这个地方不比深山,难免被人看到,那时若荐了你去,怕是不好吧?”
两人于是搬入霸陵山中,男耕女织,梁鸿闲时读书写字。即便这样,梁鸿仍然名声远扬,只好又隐姓埋名,东搬西搬,最后投奔吴中富豪皋伯通,向他借了间屋子,靠给人打工过活。
每天梁鸿做工回来,孟光便做好饭菜,恭敬地端给他。孟光每次都把盘子托得跟她的眉毛齐平,表示礼貌,梁鸿当然也是很客气地接过去。天长日久,皋伯通觉出不对头:“一个佣人,这样子相敬如宾,知书达理,定非常人。”于是把他们接来家里一起住,又管吃管穿,梁鸿才得以安心著书立说,直至晚年。
党人之祸
东汉末年,名士如流,最有名望的当属郭泰。一天下雨,郭先生的头巾被雨淋坏,一只角耷拉下来,他也不在乎,仍就如此戴着,没想到一般的名士见到后,纷纷学他的样子,专门把头巾的一角耷拉下来,还冠其名曰“林宗巾”。短短时间内,远近儒生尽戴林宗巾。
后来,天下名士与当朝宦官敌对,被指为“党人”,受到宦官迫害,“党人”纷纷招罪入狱。有个度辽将军皇甫规自认为是天下豪杰,但是跟党人没往来,没有被捕算不得名士,感到羞愧难当,便上书朝廷说曾与党人有过来往,望请治罪,但是朝廷还要用他抵抗匈奴还是没有为难他。但,榜上有名的却在劫难逃。李膺曾做过司隶校尉,深受名士拥戴,曾有人劝其逃走。李膺说道:“我若逃走,岂不害了别人,况且我年已六十,一死而已,何必再逃。”于是慷慨赴死。
另有汝南人范滂,名冠士林。汝南督邮吴导奉命去捉范滂,又不忍捉拿,到了驿舍,左右为难,手捧诏书,闭门大哭。范滂听了内疚不已,竟直接去县里投案,把县令吓得不轻,县令交出官印,情愿与他一起逃走。范滂感激道:“天下这样大,去哪不好,非得跟我自投罗网?我一逃,岂不连累于你,再者家中老母年事已高,何必又连累到她老人家?”县令无法,只好请来范母和他的儿子与他相见。临别时,范滂对儿子说:“我想让你作恶,但恶事不应该做;想要让你行善,但这就是我不作恶的下场。”众人听了,都流下了眼泪。范滂跟着吴督邮前赴京师,最终死于狱中。
但也有与之不同的,有一个张俭,不想无端送命,便到处躲藏,以致有人受他连累,或遭拷打或被处死。有家姓孔的便因他受累。张俭逃到孔家,本是与孔家的哥哥交好,但这天恰巧哥哥不在家,十六岁的弟弟问明情况,便自作主张收留了张俭。几天后,风声走露,官府前去捉拿。但张俭已逃,官府便把孔家两兄弟带回,却不知如何定罪。弟弟说:“是我招待的,应该定我的罪。”哥哥说:“他是投我而来,该办我的罪才是,我弟弟尚小,与他无关。”官吏无计,问他们的母亲,孔老太太道:“我是一家之主,正该办我的罪才对。”几人这样争着没结果,上书朝廷,最后把哥哥定了罪,结果那家的弟弟因此名扬宇内,那个弟弟就是四岁让梨的孔融。
读这些故事,兴味甚浓,看这些名士,别有一番风流。然江山百代物换星移,斯人斯事,已成传奇。
(作者单位:山西焦煤汾西矿业贺西矿)
- 上一篇:
- 下一篇: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