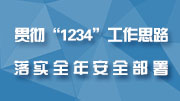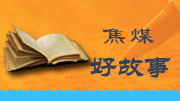每次离开老家,妈妈总会把她那些视若珍宝的老粗布从百宝箱里倒腾出来,一一摆在床上,仿佛在展览一般。她左看看右翻翻,精挑细选一些她认为花色顺眼、手工精细的老粗布让我带走。在妈妈看来,她能留给我的家底就是这些。在我看来,那一摞摞整齐的老粗布,每一款花色都是现在无法比拟的,是珍贵无价的,每一件成品都包含着妈妈辛苦的心血。
现在的孩子是无法想象,从地里的棉花到制作成一件花色的粗布需要多少道繁杂的工序。而我有幸经历过,同时也见证了时代的巨变。
我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候物质匮乏,的确良、太平洋床单、风雪衣在当时都是很奢侈的东西,谁家拥有一件那都是令人无比羡慕的。许多生活用品都要自供自给,炕上铺的、身上穿的都是自己加工制作的老粗布,所以女人学会织布在当时是必备的一项技能。从我记事起,妈妈每天就是不停地忙碌,忙庄稼,忙针线、忙织布……
粗布的制作根据棉花品质的不同分为几类:上乘优质的棉花纺线织成花色优美的炕单,大多都是为婚娶使用,这也最能凸显出女人织布的手艺;中等的棉花纺线织成日常家用的铺盖或者是纳鞋底的衬布。这在每个家庭中都是大量使用的,被面、棉衣棉裤的里布等都要用到;次一些的棉花常常纺织成笼布或者洗碗的抹布。每一个档次的棉花都不会浪费掉。
我小学的时候,也像大多数的乡村女孩一样,学习一些女红,先从最简单的纺线学起。纺线看似简单却并不容易,要配合纺车,对两手的协调以及抽线速度都有要求,否则织出来的线时粗时细,根本无法织成布料,也就成了废品。我手笨,为了学纺线浪费了许多棉花,妈妈就不再让我学了。纺好线只是第一步,如果要织成花色,还要给这些纺好的线染色。绿色、粉色、紫色、红色,这些都是妈妈常染的颜色。
最复杂工序就是要把这些线按照一定的顺序固定在织布机上,这是很神奇的一道工序。这个时候,妈妈会把家里大门关上,不让任何人打扰,因为一个花色错了,织出的几丈布就作废了。我最爱看妈妈摆线,静静地看着她摆着零件,一个花色一个花色地摆线……常常一下午就过去了。
摆好了线,就可以织布了。在忙完家务活后,妈妈就坐在织布机上,梭子在她手里穿来穿去,织布机在妈妈的操作下发出悦耳的声音。妈妈享受着劳动的快乐,我则享受着妈妈又织成一件成品的喜悦。
当我再次看到织布机时,它已经在老宅子的角落里躺了很久,上面布满了灰尘。时代的巨变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技术让女人们有时间从事不同工种的工作,新时代也赋予女性更多的社会责任。织布机、老粗布已经成为了历史,我希望它们不仅仅是历史,还希望它们能以另一种形式更好地传承下去。
(作者单位:西山煤电水泥厂)
- 上一篇:冬节已至
-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