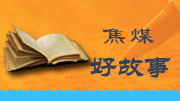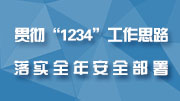一阵剧烈的咳嗽过后,老林扔下刚刚落实了政策、农转非的妻子和三个上学的孩子,走了。
日子,醮着蜜过就甜,要是醮着黄连过,那味道就苦不堪言。大林家的日子,从那时开始,就是醮着黄连过来的。
这一年,大林十六岁,刚刚接到市一中的录取通知书。
这一年,大林的母亲像男人一样,挑着担子,拿着锤子和小板凳,下了河滩,加入了砸石子的行列。
这一年,大林哭过之后,把二林、三林送到了学校,自己却没有到校报到。
这一年,矿集贸市场的角落里,多了个简易的铁皮房,大林开始了打饼子、卖饼子的生涯。
天亮了又黑,黑了又亮,大林的生活被一炉旺火点燃了。
大林知道用电烤炉轻松,但他却坚持用火炉,虽然烟熏火燎的,需要的体力也多,但烤出的饼子,外表焦脆,内里柔软,矿区的职工家属都喜欢。
靠着这一炉一炉的饼子,大林赢得了“饼子林”的称号,艰难地撑起了这个家。
二林、三林读大学的时候,饼子林的一炉旺火已经不够了。于是,饼子林那“饼子……饼子……”的吆喝声开始响彻矿区的大街小巷。
二林、三林工作了,饼子林说自己喜欢饼子的味道,依旧打饼子、卖饼子。后来,二林、三林陆续结婚了,饼子林还说自己喜欢饼子的味道。那个饼子铺,春夏秋冬,四季常开。
母亲走的时候,饼子林看着二林、三林带着家属,指挥着下属,把给母亲的花蓝整齐地排到灵棚前。他抹着眼泪,端了一盘饼子到母亲的灵位前,跪在那里,半天都不起来,“妈,妈唉……”那声音凄惨,哀惋,撕心裂肺。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二林把饼子林请到自己单位吃饭。席间,二林对办公室主任说,“这就是打饼子、卖饼子供我们弟兄俩上大学,供我们结婚的哥,你看看单位有什么适合的岗位……尽量……”
饼子林把头摇得和拨浪鼓一样,一个劲儿地说:“二林,我离不开饼子的味道……”
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三林派车把饼子林接到自己公司,指着厂房说:“哥,我的就是你的,要什么随便拿。”
饼子林指着外边的一堆焦炭说:“三林,你给我点焦炭就行,打饼子能用。”
天亮了又黑,黑了又亮。饼子林依然在铁皮屋打饼子、卖饼子。生意不好的时候也挑着饼子走街串巷,吆喝着卖饼子。只是开门的时间短了,走街串巷的机会也不多。
有人猜测是饼子林年轻时吃的苦太多,天天劳作,现在身子垮了,干不动了。也有知情人说,饼子林有个叔叔,曾经接济过他家,现在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饼子林总要抽空去照顾,不能像以前那样打饼子、卖饼子了。
五十八岁那年,饼子林孤独地倒在了炕上。邻居叫来二林、三林,问饼子林还有什么要安排,饼子林艰难地抬起头,对两个早已哭成泪人的兄弟说:“打饼子的那个炉子,十六岁就跟着我,它陪了我一辈子,让它跟我一起走吧!”
太阳照在山梁上,把出殡队伍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二林、三林身穿重孝,抬着饼子林的炉子,艰难地跟在灵柩后面。灵柩里,安静地躺着饼子林。
(作者单位:汾西矿业工程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