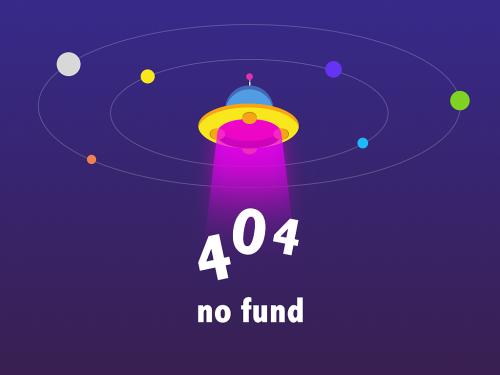1976年7月28日凌晨,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重镇河北省唐山市发生7. 8级大地震。一场由党中央直接指挥的抗震救灾战役旋即展开。当时的西山矿务局矿山救护队、医疗队不远千里,驰援灾区,同各路救灾队伍一起投入到那场气壮山河的抢险救灾中。
前方救援牵动着矿区职工和家属的心,西山矿务局决定派出记者,到救灾一线采访报道。我们一行三人搭乘矿务局给救灾队伍运送给养的大卡车,踏上了征程。
我们傍晚出发,穿过莽莽太行山,越过满是青纱帐的华北平原,经过一天一夜的艰难跋涉,终于进入灾区。灾区的景象惨不忍睹:高高耸立的大烟囱只剩半截,桥梁断裂垮塌,公路裂缝,铁轨扭曲,就连河沟边低矮的水泥坝堰都被震得七零八落。我们的心情逐渐沉重起来。
车刚到丰润县,一股夹杂着来苏水味和不明异味的热浪迎面扑来,让人不敢呼吸。进入唐山市区,楼房、厂房、平房全部倒塌,到处是断壁残垣和砖石瓦块。临时清理出的空地上,用油毡、塑料布和木板搭建的防震棚立在那里。高高低低的废墟堆上,一群又一群的救灾人员还在忙碌地挖着、刨着,仔细搜寻着遇难者的遗体。
西山矿务局救护队驻地在开滦煤矿唐山矿的篮球场上。7月28日中午,在接到原国家煤炭部命令后,矿务局立即抽调3个救护小队共35名队员从太原搭乘飞机赶赴唐山。当天下午18点左右到达唐山机场后,又乘军用卡车来到位于市区的唐山矿。
按专业职能,救护队此行是下矿井执行抢险救援任务的,谁知大地震对井下巷道、采掘工作面造成的破坏并不十分严重,除个别伤亡外,万名井下夜班职工全部安全升井。反倒是矿区地面的设施被地震破坏殆尽,损失惨重。
时间就是生命!在余震不断的威胁中,队员们立刻在唐山矿家属宿舍区展开搜救。没有工具,大家就用木棍撬、用手搬。残墙断壁在余震中摇摇欲坠,水泥块的棱尖、钢筋头随时都可能扎破手脚,可大家都不愿意停下搜救的双手。被埋的老李一家四口找到了,救护队员一鼓作气挖开通道,洞口的钢筋头横七竖八,被困家属又都光着身子,为了防止划伤群众,队员自己压在钢筋上,让被困的人从自己身上爬出来。
在又一处废墟下,救护队员发现了一位卡在坍塌屋角的姑娘。地震发生在夜间,她没穿什么衣服,说什么也不往外爬。救护队员说:“姑娘出来吧,我家女儿和你一样大,别怕!”见她还不动弹,队员们脱下自己的衣服塞进去,等她穿好衣服后,才把她救出来。搜救幸存者告一段落后,队员们又投入到搜寻和搬运遇难者遗体、下井排水、疏通巷道等工作中。
唐山灾区就是一个大战场,不时有军用卡车沿街慢慢驶来,车上站着两排女兵。她们戴着大口罩、背着喷雾器向街道两旁喷洒着消毒药水。一架低空飞行的“安—2”型双翼飞机在人们头顶盘旋,像是巡视救灾现场。一位穿白大褂的女军医来到救护队驻地,要求救护队必须赶快修建临时厕所,再不能随地大小便了。
我们又前往西山医疗队驻地滦南县采访。沿途大片的庄稼地里摊着一团团细沙,那是地震发生时从地下涌出来的。滦南县农村的房屋除倒塌损坏的外,多是整体下陷了一米多深,进门就跳坑,窗户也成了门。
西山医疗队是由矿务局总医院和各矿分院抽调的医护人员组成的,以外科医生为主。医疗队一到灾区,就马上投入到抢救伤员的战斗中。手术一台接着一台,24小时连轴转。刘大夫是唐山人,他的母亲和妹妹都在地震中遇难,但为了抢救伤员,他都顾不上回家看看。
我们在灾区采访了一周多时间,撰写了关于抗震救灾的长篇通讯和报道,还代表救护队全体队员写了一封致后方职工家属的公开信。后来,我们搭乘着军用飞机到达北京,这可是我第一次坐飞机。
这些年来,我一直关注着唐山,并几次故地重游。浴火重生的唐山已经发展成为现代化城市。在城南保留的地震遗址纪念公园里,矗立着一道用黑色大理石砌成的纪念墙,它长493米,高7.28米,上面刻有24万名遇难者的名字。纪念墙庄严、厚重而深沉。
唐山大地震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抗震救灾中彰显出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和“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民族精神和英雄气概却在华夏大地传承开来,尤其是在汶川大地震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得到发扬光大。抗震精神,属于唐山,属于中国,属于全人类。
(作者系西山煤电退休职工)
- 上一篇:没有了
- 下一篇:词两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