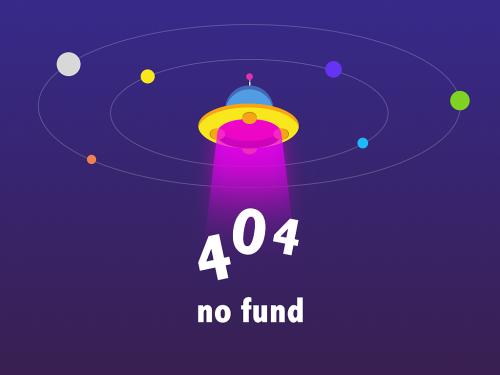摔响窝窝是儿童时代在故乡流行的一种游戏。
儿童时代是个大致的概念,按照官方的说法,十八岁之前都是儿童时代。儿童时代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就像从管涔山出发的汾河,汩汩涓涓哗哗,涌到河津,投身黄河,每一段都特色各异。
童年也是这样:六千五百七十天里,每天的太阳东升西落,不断回归;每天的色彩赤橙黄绿,缤纷各异;每天的气味咸甜酸苦,浓淡不同。摔响窝窝不过是童年时代某个阶段的一抹流行色。那个阶段过去了,街上流行的衣服变了款式,响窝窝也摔透了底子,在一声“叭”中,在阳光的剥离下,水归天,泥归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到再次流行的时候,已经变幻了主人的面孔。
摔响窝窝,大约是在五六岁的年纪。往前,身小力亏,难以抟泥成形,更不要说还要奋力摔出去,换回一声“叭”的脆响。往后,上学启蒙,渐近文明,情感上与泥土渐行渐远,那种地上爬、土里滚的亲切日渐消失。万事总有例外,玩响窝窝的孩子也不乏一些八九岁的老吊头混在其中,成为异类。
摔响窝窝,必在天气暖和时候。十冬腊月挤暖暖,初春时节野地里窜——那时节,土或者冻,或者硬,不要说孩子,老农的手指也是尽可能拢起来,远远避开的。从孟春到早秋,泥土疏松得像发面,河水温润得赛碎玉。小小巴掌,纤纤五指,挖泥讨水,正是时节。
摔响窝窝,必须得有一个台子。这台子,可以是平整瓷实的土坛、麦场,可以是戏台前端砖砌的边缘,可以是河边石垒的堤岸,也可以是井台附近水泥抹过的台阶、池沿……无论如何,这台子要很硬,才能让极软的响窝窝在粉身碎骨中升华成仙;这台子要平,才能让刹那间聚集在狭小空间里的空气爆炸开来,发出震耳的响声;这台子要超凡脱土,不容易在响窝窝的渍浸下腻腻歪歪。倒掉的石碑碑身光滑整洁,是摔响窝窝的最好台子。在故乡,石碑一般都是青石材质的。碑主的刚烈、石匠的汗水、观者的目光与指纹,赋予这存在了兆亿年的死物以鲜活。石碑即便倒掉了,依然保持着刚烈不散。
摔响窝窝,以三四人玩耍为宜。摔响窝窝有输赢,“损不足以奉有余”,几乎是所有人类游戏的核心规则。大人游戏争的是钱财权势,小孩子摔响窝窝,争的是一把能补出裂口的泥团。摔响窝窝时,没有摔响的、炸裂的口子不够大且声音不够响的、炸裂的口子够大声音够响的,是排序和输赔的标准。在同一个台子上摔响窝窝,人人独立表演,输赢却不能含糊,否则就变成了“耍诈毛”。人数太少,缺乏竞争性;人数太多,垫底的响窝窝都不够输配。
摔响窝窝,取材最原始、最容易。滚铁环、鸡毛蒜皮、翻调……这些游戏取材都比摔响窝窝更复杂。摔响窝窝,取材唯水、土而已,很像人类始祖女娲的抟土造人。土,是黄土地上最丰富的资源。人从土里来,又到土里去。人吃土一生,土吃人一口。摔响窝窝,最好选择没有料礓等杂质的黏土。水就更好说了,自家瓮里可以舀,河里可以掬,雨后形成的水泊泊里连泥带水可以一起捞。再不济,碰到在井台上汲水的邻居,叔叔伯伯爷爷大妈婶子姑姑地喊上一通,连求带劫地弄到半桶水,也够大家玩上半下午了。
摔响窝窝,也讲技巧。凡有输赢的地方都不会与技巧绝缘,只需要一把土、一瓢水、一臂力的摔响窝窝也一样。黏土与水的比例要适当,以能够站立成形为标准,太硬容易裂而不响,太软就会塌而不裂。调制泥料的过程中,先要洇,后要闷,洇和闷都要到位。要下力揉,将泥土中潜藏的气泡一个一个挤出去,让每一粒土和每一滴水充分融合,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标准的响窝窝做成以后,就像韩式碗:沿齐,壁立,底薄。摔的时候要先把响窝窝捧在手里,站起身子,缓缓地翻转手腕,在响窝窝举到最高点时,手腕也完全翻转过来,响窝窝彻底向下,加快速度到最大,增加力道到极致,狠狠地向着台子摔去。摔的地方要选平整干净的所在,保证一摔下去,响窝窝的沿儿能够齐齐整整地扣在台子上,让急剧压缩的空气产生爆炸力,顶得薄薄的窝窝底向外大翻,形成大大的裂口,连带 “叭”的一声脆响,唤起过年般的快感,这样才能赢取别人的泥团。
孩子的手掌大小相差无几,与原始的响窝窝大体相当。随着一丸丸泥团输配给赢家,终于响窝窝没法再捏,捏起了也不会再响:小小的容积装不下多多的空气,形不成爆炸条件。孩子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退出摔的江湖,隐身于看的行列。得到更多泥团输配的孩子的响窝窝越做越大,手掌逐渐装不下了。赢到最后的孩子最后一次将响窝窝做好,在所有孩子甚至还有大人的众目睽睽之下,照着自己曾经取得无数次成功、赢取了无限泥团的动作,教科书般地朝着台子摔去,“噗”,响窝窝摔成了一团结结实实的泥疙瘩。期望中自己过年的喜悦化为旁观者欢快的笑声,最后的赢者就这样结束了游戏。
似乎过了摔响窝窝的阶段后,大家就进了学校,然后迟迟早早地进入了社会,然后长到成熟,长到皱纹爬上了脸庞,爬上了额头。那些小时候一起摔响窝窝的人凑在一起的时候,会谈起少时一起偷东家梨、撸西家杏的往事,会谈起互相瞒骗家长下河游野泳的勾当,会点鼻嗔怪,会戏谑责骂,却极少聊到摔响窝窝——大约是因为,输的是泥团,赢的也是泥团,最后的赢家又在游戏结束时把大家托付的泥团一次性还给了泥土吧。
摔响窝窝的日子渐渐远去,当年的玩伴都鬓已星星,还有故人化身为新鬼。“再回首,已是百年身”,不少发小的孙辈已经到了摔响窝窝的年纪,只怕他们再也不会摔响窝窝了:他们的父母早已走出了农村,曾经粘在鞋底上的泥土在岁月的长河里荡涤已尽;他们的脚站在大地上,却不是站在泥土里,天生缺失跟泥土联系的脐带;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他们已经做到了“不输在起跑线之前很多的线上”,幼教、辅导班、特长班是生活的主流;好不容易有一点玩耍的时间,手机里的音视频,塑料制的玩具车塞满了他们的视野;橡皮泥、伸缩球倒是会变形,只是缺乏了泥土的亲切。更不用说,我们的民族似乎已经将泥土与不卫生画上了约等号。泥土已经不再是他们的玩伴,哪里还会摔响窝窝呢?
“叭”,三四十年前摔响窝窝的清脆声在耳边响起,萦绕脑际,久久不去……我真担心,这“叭”的一响,会成为生活乃至传统的绝响。
(作者单位:集团公司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