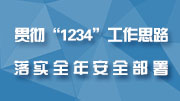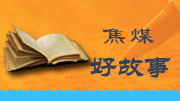爷爷是饿死的。那是1948年青黄不接的初春,连续几天米未沾牙的爷爷撇下了奶奶和他生育的三男两女无奈地走了。奶奶刚刚三十岁,父亲三岁,是家里的小幺。当时家里穷得置办不起一口薄皮棺材,只好用家中仅有的立式柜子装殓了寒苦一生的爷爷。这一幕,成了奶奶心里永远的伤痛,常挂在嘴边的遗憾,深深地烙在父亲幼小的心灵里。
我从四五岁时跟着奶奶生活。夜幕降临后,就窝在她的怀里,听她讲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往。奶奶十五岁嫁入张家,三十岁的妙龄就扛起了生活的重担,拉扯着如葡萄串一般年龄相差无几的五个儿女。奶奶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每天只是佝偻着腰不停地劳作,过早地弯曲了脊梁。“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奶奶似乎很快步入了老年,面容粗糙,沟壑纵横,原本纤细柔软的手掌变得干裂,骨节粗大,眼睛里没有光彩,神情疲惫哀伤。
父亲说,儿女的骨肉都是母亲用汗水、泪水和血水和着泥水团成的。岁月流年中,孩子们渐渐长大,虽然都一样的瘦骨嶙峋,但个子都窜得细长。父亲虽是小幺,却是最聪慧早熟的一个。在和哥哥姐姐们一起割草砍柴的忙碌辛苦中,功课却没有落下。年仅十六岁的他考入了山西财经学院。然而由于学校的变故,父亲无奈返回家乡务农。他虽万念俱灰,但还有一颗不甘心、不罢休的躁动之心。
他总是沉默寡言,对传统观念和做法不屑一顾,不愿苟同,作为村里仅有的高学历孩子,他对一些传统观念常有独特的思考和判断,并执拗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大人据理力争。端午节,为了长久保存粽子,大家都把蒸好的粽子泡在凉水里。父亲认为这样加快了细菌的滋生速度,便把蒸好的粽子藏到窑洞的后屋,因此遭致奶奶的扫帚加身。
1962年,人们把裤带勒得更紧。父亲肚子空空却满脑子想法。在无法向土地多索取一口吃食的失望中,他决定要学一门手艺,那就是到洪山公社联办陶瓷厂去做小徒工。
当时的洪山村山清水秀,黛色的山峦满含着铝、铁、硅、钙、镁等矿物质。据考证,洪山制陶的历史可追溯到唐贞元年间,距今已有千余年。源神泉水和洪山陶土为洪山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洪山窑是北方典型的民窑,当时烧制粗瓷碗、盘、碟、酒具的小窑星罗棋布,洪山村也有自己的村办企业。
父亲是苦水里泡大的,当学徒时不惜力气,为了能早日学会“捏碗”的技艺,他担负起了搅砂轮的工作。当时没有电机,搅砂轮全靠人力推动。在日复一日的咬牙坚持中,父亲的胳膊日渐粗壮,肩膀日渐厚实,通过用心观察,偷艺学习,聪慧灵性的父亲技艺不断进步,很快成为了陶瓷厂正式的捏碗师傅。他为了多挣工分,新婚没几天就离开家。父亲心无旁鹜地守在厂里,夜以继日地沉浸在砂轮的转动中。父亲说,他是真的迷上了这一活计,指尖触碰如婴儿肌肤般柔滑凉腻的泥胚,就像遇到了恋人。后来,他撇下不足百日的我和母亲去汾阳打工,制陶技艺日渐精湛,还练得了一双识别原料的火眼金睛。
1978年,三中全会的春风复苏了整个中国大地。村里的广播充满激昂的声音,传达着新的改革讯息。土地实行承包,包产到户,预示着有能耐的人可以大展拳脚。金黄的麦浪绵延向远方,打谷场上大人们用俚语打趣逗闹,小孩子们则蹦跳疯跑着穿过场院。洪山泉水在沟渠里奔流而下,如瀑布般冲击着木质的轮盘,带动水磨日夜不停地转动,转出阵阵麦香……蓬勃而希望的田野景象也让人们萌动了心头的希望。
982年的初春,当跟随奶奶生活多年的我和妹妹听说父亲从外地打工回来时,我们俩拉着手笑着、跳着,飞跑着去见他。风尘仆仆的父亲形容消瘦,一身疲累,但眼神晶亮,眼角挂着笑意。我和妹妹见到他以后哇哇哭着抱紧,生怕一松手他就又会消失不见。时隔不久,父亲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独立承包了村办陶瓷厂。
创业很难,父亲却从未想过放弃。他说:“装你爷爷的那个柜子,压在心上,我从没卸下过。我得让家里人生活好。”洪山虽有陶土,但只有懂行的人才能找到分布点。父亲是个用心的人,干一行爱一行、懂一行钻一行,在十多年废寝忘食的坚守中,原料从哪来,熟谙于心。然而要垫付的资金却是没有的。父母冥思苦想,终于找到了灵感。当时男人们流行戴帽子,军帽和鸭舌帽是首选。母亲向当裁缝的二姨好好请教了一番,先画出帽子的纸样,进了军绿色和褐色的毛哔叽料子,在缝纫机上加工帽子。母亲的缝纫机日日夜夜地转动着,父亲则每天背着一包袱帽子四处售卖,我清晰地记着父亲晚上回来握着一沓毛票让我好好数清楚的情景。这就是父母捞的第一桶金,也是陶瓷厂的起步资金。
陶瓷厂投入生产后,为了找市场,父亲又开始了长途跋涉。他骑着自行车驮着沉重的盘碟碗罐到处寻找客户,有时一天要走百十多公里。虽然跑得辛苦,但每天都有收获,驮出去的瓷器也都有了下家。在父亲的咬牙坚持中,厂子运转逐渐进入正轨,送料的主动上门,买货的主动联络。父亲以真正的行家做派掌握着每一道工序:原料入厂把关、泥胚成型、烧制火候、温度掌握、出窑时间……一时间,高品质的产品声名远扬,客户遍布三晋大地。
随着市场的不断变化,父亲脑子里又有了新的想法,他开始琢磨着研发新的种类与样式,碗罐、盘碟、花盆、大瓮水缸,后来开始烧制专供焦化厂使用的耐火材料。八十年代,介休的炼焦产业风起云涌,耐火材料供不应求,父亲的事业也蓬勃发展,一时红红火火,成为当时远近闻名的万元户。可父亲低调而谦逊,无论人们说什么,他都只是嘿嘿一笑,依旧穿着油污浸染的粗布工装,袖口和下摆磨出的棉线随着他奔波的身影在风中飘动摇曳着。
父亲五官周正,棱角分明,面容英俊,但唯一的缺点是早早就佝偻起背脊,也许是因长年劳作且还在低矮的瓷窑中钻进钻出形成的。那背脊上像永远扛着一份担当,一份重任。是的,父亲扛着的不仅是自己家人的吃穿用度,亲戚、朋友、邻里的困难也是他解决的范畴,除了接纳他们的子女在厂子里工作,每逢上学、婚丧嫁娶等大事他都要慷慨解囊,但往往是借多还少,甚至有借无还,父亲却从不在意。村里的公益事业,村主任第一个就会想到他,因为他最好说话,最大方。但在对待自己时,他吝啬如葛朗台,对吃好的、穿好的深恶痛绝,直到现在还蜗居于早已停产的厂子里,穿着破旧的工装,弯腰低头侍弄着他开辟的菜地,吃着白皮面,就着辣椒葱蒜,抿着便宜的散酒怡然自得。哪怕女婿们拎去茅台、五粮液,他都会皱着眉头连连说不好喝,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贵。
父亲说,他是真正尝到改革开放甜头的人,没有三中全会就没有他的创业机会,没有好政策他也许一辈子是个穷光蛋。父亲一生谨守本分,没有再拓展事业,时至今日,他还有些后悔自己当时固步自封,没有听邓小平老人家的话“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如今,父亲已是古稀之年,依旧躬耕于农田,从不懈怠,享受劳动带给他的充盈与安然,享受着属于他的春耕秋收。
(作者单位:汾西矿业党委宣传部)